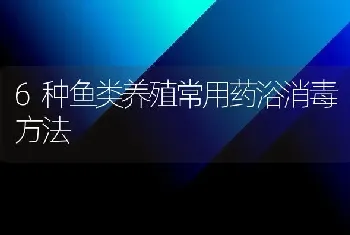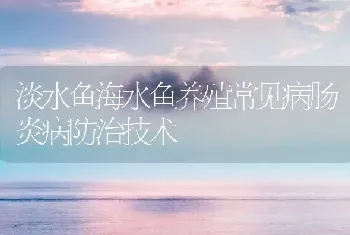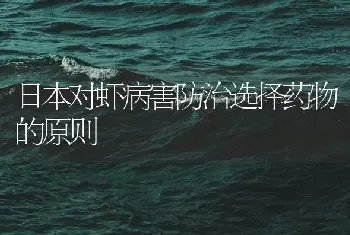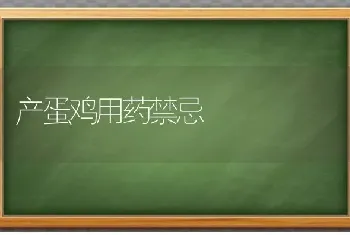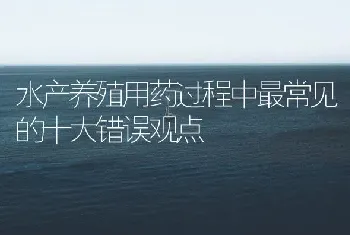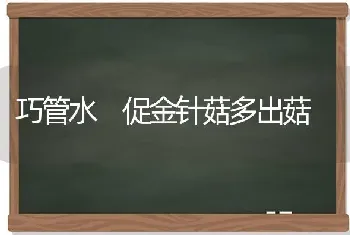渔药这个名词最先源自于1997年农业部《渔药手册》编辑委员会编撰的《渔药手册》,此后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渔用药物使用准则》(NY5071-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渔药使用规范》(SC/T1132-2016)等标准中予以进一步认可。渔药属于药物的范畴,它是为了提高水产养殖产量,用以预防、控制、治疗和诊断水产动植物病、虫、害,或者有目的地调节其生理机能,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促进养殖对象健康生长,以及改善养殖水体质量所使用的一切物质。渔药必需受到国家药事法制约。

“渔药”从它诞生之日起,有过它的辉煌,因为它对我国水产养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也走过着很多彷徨的路程,充满着不少尴尬的局面。时至今日,渔药这个名称还没有被官方认可,以至五花八门的名字簇拥着它:水产养殖用兽药、渔用药物、水产药、水产养殖动保产品、水产养殖投入品、水质/底质改良剂、非药品等等,无形中给它罩上了一种既不正统、也很随意的外衣。渔药是因水产动物疾病而诞生,也随着水产动物疾病研究的深入而发展,我们从它诞生、前行过程中的一组数字,即可看清我国”渔药”所走过的历程,蹒跚的脚步以及未来的道路。
1000多年以前。
我国渔药的诞生和应用有着渊源的历史。早在1000多年以前,北宋苏轼(1030-1101)在《物类相感志》中就曾描述,“鱼瘦而生白点者名虱,用枫树皮投水中则愈”;此后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1628)也曾指出,“鲺如小豆大,似团鱼,凡取鱼见鱼瘦,宜细检视之,有,则以松毛遍池中浮之则除”;这里所指的“枫树皮”、“松毛”等就是最早的渔药原形。这些发现要比欧美公认的发现者Baldner(1666)要早数百年和数十年,渔药源自于我国当之无愧。
老3样。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水产养殖业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养殖密度较小,集约化水平低,纵然时有疾病发生一般也不太严重,不会造成疾病大规模的暴发和流行,损失也较轻微。在这个时期渔药主要是针对鱼塘的消毒和应对一些并不太严重的寄生虫鱼病,因此使用的渔药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化学类药物,如生石灰、高锰酸钾、食盐、硫酸铜、硫酸亚铁、敌百虫等,其中生石灰、硫酸铜和敌百虫使用最多和最频繁,而且能基本解决水产养殖中存在的大部分病害问题,因此人们在一个比较长期的时间内将其类称为“老三样”。这个时期渔药发展相对滞后。
第1。
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了渔业“以养为主”的方针,水产养殖高速发展,养殖产量逐渐超过了捕捞产量,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水产养殖大国。随之水产动物病害也日趋严重,如草鱼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等主要淡水养殖鱼类暴发性流行病一度威胁着水产养殖的健康发展,解决这些疾病造成的危害成为国家重点攻关的研究课题。从80年代末期开始,科研人员通过对病原、病理、流行和防治深入研究,带动了渔药应用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一大批防治病毒性鱼病、细菌性鱼病、真菌性鱼病以及寄生虫病的渔药。经过11年的研究,“鱼服康”于1988年成为我国第一个有组方、有批文、名正言顺的防治细菌性鱼病的商品渔药产品;通过药效、稳定性、毒性毒理、残留、生产工艺、临床试验以及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研究,“鱼用强氯精”于1998年获得了由“农业部畜牧兽医司药政处”颁布的第一个国家标准的消毒剂渔药产品,由此带动了次氯酸钙、氯铵T、二氯异氰脲酸钠等消毒类渔药在鱼病防治上的应用;菊脂类杀虫药是摒弃传统的杀虫理念,采用高毒性农药原料合理应用于水产上的第一个高效杀虫类渔药制剂,曾以“灭虫精”、“灭虫王”等商品名疯迷于渔药领域,神奇地解决了水产养殖中的中华鱼蚤病、锚头蚤病等寄生虫鱼病的流行,深受养殖户的青睐。借助以上一些第一个渔药制剂的生产、应用和推广,我国渔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大地,带来了我国渔药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产值升至4亿元。
农业部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1994年发布了《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则(试行)》,并决定自1995年7月1日起对渔药生产企业实施GMP管理,各地新建的生产企业必须经过GMP验收合格后,才能发给《兽药生产许可证》”;在2005年12月31日前未取得《GMP合格证》的渔药生产企业,将被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不得再进行生产。在这种新的要求下,我国的渔药生产企业开始迈出了正规的步伐。2004年底我国专业生产渔药的企业就达150家,附带生产渔药的兽药企业有300余家,全国有近450余家的生产规模,生产品种达500余种,年产量2.5万吨,产值达4亿元以上(仅为有国家和地方标准的渔药制剂,不包括微生态制剂等),已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187个渔药制剂升为国标渔药。
2004年11月9日农业部发布了426号公告:在2005年前,“清理兽药地方标准和换发原兽药地方产品批准文号”,兽药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即“地标升国标”)。2005年6月13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渔药企业地方标准升国家标准研讨会”,并由93家渔药企业以及6家农业部渔药临床试验单位成立了地标升国标技术协作组。协作组对业内企业提交的334个渔药地方标准审查后选定了其中的237个委托农业部渔药临床试验单位进行临床试验,开始了数年的渔药地标升国标的历程。渔药地标升国标是我国渔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对规范渔药的生产和销售、确保渔药的使用安全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截止2009年年底该工作结束,187个渔药制剂(剂型)获得了国家标准,除个别稍后被取消外,大多数一直沿用至今。
“非药品”产值达100亿元。
渔药地标升国标后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造成了水产动保产品(“非药品”)充斥市场,水产动保(“非药品”)企业快速膨胀的局面,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困扰着我国渔药的管理和使用安全。地标升国标后,有一大批无法升为国标的渔药产品,特别是水质(底质)改良剂,用于调水的微生态制剂,由于养殖生产的需要,只能以动保产品(“非药品”)的名义与国标渔药“水火相济,盐梅相成”。进而在这类产品的掩护下,有些安全性不明或存在较大问题的化学类抑菌杀虫药物、灭藻药物、消毒药物也以这种形式充塞渔药市场,造成了若干乱象。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国有水产动保(非药品)生产企业近2000余家(包括部分GMP企业),经营企业达20000多家。水产动保(非药品)涉及的商品达10000余个,产值100亿元以上,占据渔药产值总额的8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90%。除此之外还有较大量的肥水类产品。这种水产动保(“非药品”)产品导致了管理的盲区,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方面的8大成果。
20世纪未到21世10年代,随着全社会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人们认识到渔药使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控制其风险,合理使用是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措施。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攻关课题、863计划、农业部行业专项等重点项目的资助下,我国研究人员在渔药理论基础与应用实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绝的成绩,为建立“渔药药物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1)强化了渔药应用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通过渔药代谢酶、渔药作用的受体,从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探讨了渔药作用的机制;通过渔药在水生动物体内药代动力学模型,摸清了几类的主要渔药的代谢、消除以及在水生动物体内的转运、转化规律,并为建立了相应的检测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撑;根据水生动物的特点,阐明了影响渔药作用的若干因素。(2)深入进行了抗生素、氟喹诺酮类、磺胺类以及杀虫类等渔药在主要水生动物体内的药代动力学研究,获得了相应的药动学参数,为渔药的合理使用提供了依据。(3)提出了孔雀石绿等有毒有害化学类物质在水产养殖中使用的危害及其禁用,研制出替代孔雀石绿的药物制剂“复方甲霜灵粉”(“美婷”),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美婷”是自2005年地标升国标之后第一个获得药证和药号的化学类渔药制剂。(4)加快了新型渔药创制的研究。在中草药、杀虫剂、渔药增效剂以及免疫增强剂和生长调节剂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成果,推进了渔药产业的发展;在微生态制剂的功能、生产以及使用等方面创建了很多奇迹,在水生动物病害的生态防治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开展了消毒类渔药片剂、颗粒剂以及大丸剂,口服类渔药微胶囊缓释剂,壳聚糖纳米粒剂等剂型的研究,将渔药的生产和使用推向了更高、更广、更深的境界。(5)建立了渔药的微生物法、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免疫学法等检测方法,并建立了一系列相应的标准,研制出部分检测试剂盒,为渔药的残留检测和监控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保证。(6)开展了病原微生物的耐药机制及控制耐药策略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耐药性普查和监测,为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水生动物疾病的控制奠定了基础。(7)推进了渔用疫苗的研究和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在渔用疫苗的研制上普遍应用,除了灭活疫苗外,抗独特型抗体疫苗、基因工程疫苗等也应用到水生动物疫病的防治上。截止到2020年底,我国已有9个疫苗获得新兽药证书。(8)综合在渔药领域的研究成果,建立了我国渔药风险评估模型,阐述了我国渔药使用风险及其控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情况提出了我国渔药管理的相应措施,并在我国主要水产养殖区建立了风险可控的示范区,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了困扰我国水产养殖长期安全发展的难题。
1号文件。
2021年1月7日农业农村部颁发了“关于加强水产养殖投入品监管通知”的农渔发[2021]1号文件,它以一个强烈的信号暗示水产养殖投入品乱象已严重威胁到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威胁到水产养殖的健康发展,到了不能容忍、非要下力气强力整顿地部。对于水产养殖投入品进行管理,早在2019年1月11日十部委就提出了《关于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意见》;2019年9月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发布了《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19年1、2号》,提出了在水产养殖中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76种,应依照兽药进行管理的水产动保产品257种,对水产养殖动保产品进行了初步界定;2020年5月12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公布了《依法按兽药管理的水产养殖用物质类清单的公告》(征求意见第二稿),提出了与治疗、预防相关的“水质、底质改良剂”、“消毒剂”以及“微生态制剂”等全面纳入水产养殖用兽药管理,将生产、经营和使用所谓的“非药品”、“动保产品”的行为定义为非法行为。1号文件是对以上精神的进一步强调与宣誓,其正确性和必要性已是无疑,它也是为我国渔药迈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个重要信号。但是1号文件颁布后,也导致了一些尴尬。面对1号文件,大多数动保企业(包括某些GMP企业)采取了二种行动:一种是改说明书、改包装,另一种是将动保产品改成饲添产品,改成与水产养殖不关联的产品,换汤不换药,目的仍旧是尽量逃避监管,而不从本质上去解决投入品的安全性问题。面对1号文件,监管部门似乎无能为力,其中有着二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文,对所面临的执法问题找不到依据,显得束手无策,不敢贸然行动;另一个是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无法按照1号文件的设想以使用者为执法切入点对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面对1号文件,广大的渔(农)民更是不知所措,其中存在着二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一养殖生产中必需要进行改底、改水或肥水,这类的投入品不得不用,但“用了”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得而知;其二水产养殖的病害问题仍旧是他们所面对的心腹之痛,不用那些“动保产品”怎么办?因此导致了1号文件颁布时的“电闪雷鸣”很难得到执行过程中“暴风骤雨”似的呼应。
3点看法。
渔药曾走过了辉煌的发展历程,它对我国水产动物病害的控制以及水产养殖的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就连有颇多微词的那些个“非药品”在它10多年的经历中,也曾对减少传统药物的依赖,降低抗生素的使用量,填补渔药不足的空白起到过一些作用。但是很多年来,人们对渔药看法大多是它的副面效应,罄竹难书地“控诉”它的不安全隐患,而且普遍认为产生隐患的原因是渔药科学水平低,渔药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以及养殖户的违规和违法。笔者认为,我国“渔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是这些,而根源是管理!回想2005年“地标升国标”的良好用心到后来却逐渐演变成“非药品”在我国的泛滥的局面,(2021)1号文件强势颁布的初衷而最终呈现出只闻雷声不见暴雨状况,这无不感到我国渔药领域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无不与管理习习相关。笔者的看法是:我国渔药的管理,应该要从管理理念、管理法规和管理方式上有所转变。
①渔药管理的理念应该遵循我国水产养殖的特点。作为水产动物病害防治三个手段之一的“药物防治”,渔药是不可能被消灭也不可能被取代的,即使渔药使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也不能因噎废食。要认识到我国是世界上第一水产养殖大国,我国的水产养殖在世界上处于领袖地位,对于渔药的管理国外没有借鉴。那种认为我国渔药种类不需要那么多,动不动就与欧美国家进行比较的观点是不现实、也不正确的。要认识到渔药不同于兽药,它与兽药相比有着不同的属性,把渔药划分成兽药范畴,按兽药的标准管理渔药是不科学、也不客观的。要认识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的经济基础、科学发展、居民消费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不能和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也不能用欧美国家的标准衡量和评价我国的渔药企业。要正确地处理好发展与其它各方面的关系,某些片面的举措有可能会设置道道不可跨越的“鸿沟”,所带来的并不是意想中的结果。
②渔药管理的法规应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除了《无公害食品渔用药物使用准则》等极少数标准外,我国还鲜有针对渔药的立法,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不是其它法规被不合理的套用,就是无法可依、无据可循,有些“文件”、“通知”发出后均成了一纸空文而无法落实,出现了管理的盲区和真空,渔药使用的安全成了一个永久的无底洞。
③渔药管理的方式应该符合我国渔药发展的现实。渔药由谁管理一直是在争论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外行管理内行、外行管不了内行成了渔药管理方面最大的障碍和弊端。渔药管理的主体应该从《兽药管理条例》立法开始,让水产养殖的管理部门成为真正的渔药管理主体。
0。对“0”肤浅的认识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深层次地去考虑,“0”不仅有,而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占位作用,没有“0”,“109”就成了“19”。虽然有的时候“0”似乎代表最小,但更多时候它却代表着最大,从零开始寓意着后面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笔者认为渔药的未来就是这个“0”!不容否定,渔药一定会再从零开始,一定会在“1”后面加上那些个更伟大的、若干若干个的“0”。